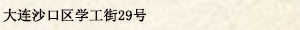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三等奖诗酒趁年
卷首语
年12月,我们开启了首届“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”,年9月30日完成了征稿环节,共收到参赛作品篇。经过多位评委的认真评审,最终评选出了8部精品作品,30部优秀作品。
现将获奖作品进行刊登连载,今天,我们将刊登三等奖作品——《诗酒趁年华》。
▂▂▂▂▂
诗酒趁年华
吕洋
第一卷天下风云出我辈
第四回环中环家国梦复醉里醉衾帏轻扬
窈儿最近好是郁闷,自小出生于那秦晋大户、名门世家,家教颇严,爹爹杨金熠更是不让女孩儿出门闯荡,壶口剑派的上好武功也不让学,只是让她在闺阁之中绣绣花儿、抚抚琴儿罢了。只是那花儿总归绣得一团团的不成样子,那上好的焦尾琴也不知道被自己砸烂了几把了。近日里闲得无聊,总想出去走走玩玩,便叫自己的贴身侍女千禧窃了一件男子衣裳出来,怎料那倒霉千禧又糊涂又胆小,只拿了下裙,却没拿上衣,使得自己穿着像个浮夸的公子哥儿。好不容易化名那“上官青云”,背着爹爹和旃檀哥悄悄溜了出来,半路上却遇见了个醉鬼,本想去灌醉了好生取笑他的,却被他狠狠占了把便宜,自己也似那丧家之犬一般仓皇而逃。此番受辱,实在难堪。可恨,可恨!
陆扬倒是潇洒得很,饮了快有六斤上好的杏花村,跌跌撞撞出了门,回了旅店倒头便睡去了。醒来已是次日晌午了,头倒不痛,身子也舒泰得很,缘那好酒本就不造宿醉,再加上南屏功法一通透,将那酒劲一丝丝地化入气海之内,又涌入了陆扬的四肢百骸之中,酒一醒,人也神清气爽,手足也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陆扬忙剥了两只橘柑,去了去身上酒气,聊以掩耳盗铃,一看床头,有两块干净的面巾正泡在木盆中。陆扬心头一暖,知道婉儿昨晚定是来照顾过了。便推开门去找婉儿与陆银桂二人。
陆扬敲门进去,陆银桂已是不知所踪,只余婉儿坐在床角,一针一针地绣着一只如若荷包一般的物事。婉儿一见陆扬,眼中顿时露出了些关怀之意,却又轻哼一声,将手上的绣物掷到床上。陆扬知道婉儿定是为他喝酒懊恼呢,忙搜刮起脑中的所有词汇来,绞尽脑汁、费尽心思去哄女孩儿。婉儿一开始也只是不甚理睬,陆扬哄了足足有半个时辰,才盈盈转过身来。陆扬一见婉儿脸上愁云满面,杏眼中甚至还氤氲着泪雾,有些惊惶,忙道:“师弟知错了,下次定不会如此放浪形骸了!”
“唉,你这个……冤家!”婉儿终是耳根子软,叹道,“下次……别再饮那么多酒了。”
陆扬忙道:“好婉儿,没有下次,定是没有下次了!”
“谁信你这油嘴滑舌的家伙!”婉儿嗔道。
陆扬见女孩儿好歹不生气了,便起身作揖道:“师姐之命,师弟可不敢不从!只是师娘……这也没见着的,倒是去哪儿了?”
婉儿不禁莞尔,笑道:“没个正经,还在这儿装正经呢!娘见你又喝成这个样子,心里也生气,就先行一步去那杨府了。我……我实在看你怪可怜的,抛下你一个人——也不大好吧,就等着你呢。快些收拾干净了,咱们好去那杨府找娘去。”
陆扬也闻见自己身子上一股酒味儿,就连柑橘的香氛也掩盖不掉的,忙回屋换了件衣裳。回身去寻婉儿时,婉儿正摆弄着他那把青钢宝剑。婉儿见他来了,将剑扔给了他,自己却垂下头来不言语,隔了半晌,才幽幽地发了声:“这是旧年在西子湖畔摇下的桂花儿,我拾起来晒干了,装进这只香囊里头去了。就系在你这把剑上吧。”
婉儿眼望向别处,似是不经意地说道,声音却羞得要滴出水来了一般。
陆扬心中涌过一阵暖流,携着婉儿的手道:“婉儿,你真好!这香囊……我定不会相负的。”说罢,使劲闻了闻香囊,笑道:“好香!婉儿就是能干!”那香囊工整纹绣着西子六和塔的模样,里面松松软软的桂花儿同棉絮一般,涨得鼓鼓的,飘荡着一股子别样的幽香,却像极了婉儿身上的味道。
婉儿忙抽出自己的手,声若细蚊道:“走啦,去找娘去。”
此时已过了晌午了,晋阳热闹的午市犹未央,大街小巷仍传着些许带着北方口音的叫卖声。陆扬携着婉儿走着,一路上也买了些吃食与玩意儿来逗婉儿开心,婉儿还是心软,不一会儿,笑颜也如这春日的榴花一般绽开了。日光流金,映衬了江南温婉女子的巧笑嫣然,倒吸引了路上许多过客的目光。路过昨日那天香食府,陆扬笑道:“这家有名气,菜也好吃,下次咱们到这儿来尝尝几味晋阳名菜。”婉儿嗔道:“我才不去!你又要饮酒!”陆扬打了个哈哈,心里却忆起那诳自己饮酒的男装女孩儿:“唉,她自言是杨金熠的义子,也不知去了这朱府,能不能再碰面了。若是再见,定要好生赔礼一番。”
不一会儿,二人便到了那朱家大院的门口。陆扬叩响了那朱红大门的雕花门环,不一会儿,一个小厮开了门,打量了陆扬两眼,随即恭敬道:“想来这位便是陆公子了,请进。”陆扬笑了笑,便同婉儿迈了进门。刚到大院,远处便传来如玉石锵锵般的笑声:“想来这位便是陆兄了,旃檀久仰了!”便从正堂里走出一位翩翩贵公子来。那公子身着一袭玄衣,腰悬一把黑剑,裙系绛朱宫绦,双衡比目螭龙佩,眉如墨画,鬓若刀裁,双目炯炯有神,似是清夜星月一般耀着光华。陆扬见那公子眉眼,总觉得有说不出的亲切来,似是在哪儿见过似的。那公子疾步上前,向婉儿微微颔首道:“婉儿师妹好。”便携着陆扬的手道:“常听家父说起南屏首徒人品相貌一表人才,如今见了,果真温润如玉!”
陆扬笑道:“旃檀兄谬赞了,早闻世兄有雄韬伟略,今日一见,果真是名门风范。”婉儿见陆扬两人虽是初次见面,便如此熟稔,互相吹捧起来也面不红心不跳,不禁一阵好笑,也装模作样道:“二位初见便意气相投,果真是少年英雄惺惺相惜!”陆扬、旃檀二人齐声道:“不敢,不敢!”旃檀道:“二位请。”便引陆扬二人进了堂内。
原来那公子姓名朱旃檀,乃是龙城朱唐家的大公子,拜在“龙城义贾”杨金熠门下,学得一身好功夫,为人又旷达,喜结交,好广游,江湖上也有“龙城多俊秀,旃檀独一档”之言。朱家乃是龙城独一档的大户,家主朱晋廷乃是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后,因天下分崩,五朝更迭,石敬瑭弃置燕云十六州,借辽兵攻入洛阳,篡帝改朝为后晋,后唐遗民便又流落到晋阳来。李存勖本是沙陀之后,复姓朱邪,于是,后唐遗民取首字“朱”为姓,定居晋阳,这一支人氏便流传至今。数十年来,龙城朱家从未忘却祖上“中兴唐祚”的祖训,朱晋廷更是同“龙城义贾”杨金熠结为兄弟,共创了秦晋一带赫赫有名的“壶口剑派”。朱旃檀乃是朱晋廷独子,又是壶口剑派的大师兄,武功了得,曾以一招“壶口飞剑”一人击败了五虎门的五位长老,独身化解了晋北的派别之争。旃檀也曾闻江南“诗酒剑”陆扬的名声,早有萌结交之意,今日一见陆扬,一柄长剑一壶酒,一袭青衫一卷书,果是儒雅俊逸的好侠客,二人乃是年轻一辈的翘楚,相见便如故人,皆大欢喜,一路上又有说不完的话儿来。
朱家豪奢,盘龙雕花柱,飞檐迥架空;楼高俯渭河,金阁翔丹红。朱家大堂上挂着一道悬匾,上有几只银勾铁划的苍劲大字,书道:“朱唐正庭”,两边侧匾上又龙飞凤舞地写道:“炎黄凤栖处,贞观龙兴时”。陆扬一见,暗自咋舌道:“这家主人雄心不小!想来太行一脉正是炎黄二帝凤起之地,亦是唐太宗龙翔之处,朱家主人竟要‘见贤思齐’么?”
大堂内也宽敞,远远坐着三人,其中有一位身材高大、留着苍白长髯的华服老者座列当中,面相威严;旁边有位蓄着鼠须、戴着高帽的肥胖中年男子,笑容满面、和蔼可亲,正抱着一把算盘,同那长须老者攀谈着。再次席,则是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女子,衣着华裳、鬓摇翠钗,那便是师娘陆银桂了。旃檀向三位俯身一揖,道:“父亲,师父,师叔,陆扬师兄与婉儿师妹到了。”陆扬向三人作了一揖,婉儿也盈盈道了个万福。那长须老者微微点了点头,向陆扬看去,目湛精光,笑道:“不错的后生哥!”又转向婉儿道:“小姑娘现在也长这么大了。”陆银桂向陆扬道:“方才还谈起你呢。你金熠师叔定要说你是武林中年轻人的佼佼者,我看呐,平日里尽是好酒耽事、放荡不羁的,一点礼数也没有,只会念两句歪诗,剑也不纯熟,又何谓‘诗酒剑’的雅号?”
陆扬赧然不语,只是憨憨一笑,那蓄鼠须的肥胖男子笑道:“饮酒不耽买卖!我杨金熠做了多少人情买卖,上至赵宋皇帝,下至落魄游侠,这些人脉关系,又有多少是那琼浆玉酿中得来的呢!饮酒一方面,武功一方面,人品又是一方面。银桂师姐这么说,可是要做蚀本买卖的!”说罢,抖落抖落算盘,哈哈笑了起来。那苍白长髯的高大男子也笑了起来,道:“龙城义贾说买卖经呢,大家还不洗耳恭听?”那鼠须男子道:“老朱莫要取笑,银桂师姐面皮薄,你尽管去笑她去,我老杨面皮子厚,留了一辈子的胡子,都没能扎破面皮呢!我可不怕你笑话!”于是众人又笑了起来。缘那鼠须男子便是要做寿的龙城义贾杨金熠,而那苍白长髯的男子便是壶口掌门、后唐遗民朱唐朱晋廷。
陆银桂笑道:“陆扬,你师娘今日在此,可没少被他们笑话呢。你杨师叔说本派南屏剑法比不上他们壶口一剑,只需一剑,便能找出破绽,点将开来。”杨金熠捻须笑道:“银桂脾气还是如十余年前那般不依不饶的,在下只是无心之语,这不,又被她抓着把柄了!也好,旃檀,你二人本是世交,今日一见,彼此定是相投机的,不如就比一比剑,看看是他南屏首徒厉害,还是我壶口首徒更胜一筹!”
陆扬忙道:“这怎么敢当!旃檀兄赫赫大名,晚辈远在江南便有所耳闻,武功想来定是极高的,晚辈又怎敢造次前来挑战呢!”
陆银桂道:“陆扬,比就是了,旃檀武功造诣早就登堂入室,你二人多交流交流,也对你武功进境有好处。”旃檀也道:“师叔谬赞了。陆兄莫要过谦,且与小弟过两招,小弟也可向陆兄多讨教讨教剑道守御的学问,算是偿了夙愿。”
陆扬见实在推不过了,见旃檀眼中又带着星耀般的光华,似是极为期待与自己论剑一般。杨金熠笑道:“旃檀平日里时常念叨呢,天下少年出英雄,南屏诗酒剑算是一档。我这徒儿可会做生意,总归是放低姿态来以情相迫的,嘿嘿,陆扬师侄,你这买卖,不买也得买了!”
陆扬听了,难却好意,便取下配剑青钢来,道:“旃檀兄,点到为止罢了,请!”
旃檀本也是好胜之人,心中一喜,笑道:“来,陆兄,咱们到中庭去。”便引陆扬退了十余步,到了一处宽阔地方。
杨金熠奇道:“陆贤侄好大能耐!这梅剑青钢,又是花几两银子淘来的?”
陆银桂却也凑趣,淡淡道:“人情买卖罢了。”
陆扬听了,想起梅点墨那割了块肉一般不舍得神情,心里不禁也一乐,将剑出了鞘,便做守势。朱旃檀知南屏剑以拆招卸力为长,不敢轻敌大意,也将所配玄剑出了鞘,道一声:“得罪了!”便直直向陆扬刺去。
陆扬见旃檀此一剑来势甚猛,忙端剑做守式,稳重敦厚似那南屏山,一招南屏暮钟,剑柄下挫,剑尖斜上挑,护住自己胸口的华盖、玉堂二处,意欲将来剑挑离。旃檀见陆扬不拘泥于固有剑法,第一招竟是收剑行礼所用的南屏暮钟,心里喜道:“这陆兄果然不同于别的庸俗剑客!”扭转剑势,又向陆扬腹部的太乙、天枢两处大穴攻去。陆扬将那青钢剑平平一削,一招朴实无华的“平湖秋月”,挡住来剑。这青钢剑本就是一等一的宝剑,而朱旃檀所配玄剑更是来头不小,竟是以那金石烈火融天外陨铁,耗费了十余名工匠七七四十九天的功夫才勉强铸成的。成剑那天,一名西域巧匠见寻常冷水无法凝剑,竟然将火红的雏剑抱在自己身上,直直坠入了水银池子中去。这剑又沾染了血气,变得锋利异常,凡是佩戴过此剑的侠客,要么成就了无上的丰功伟业,要么杀人如麻、嗜血狂暴,最终堕入魔道。百余年后,此剑因机缘巧合,又落入了壶口剑侠朱旃檀的手中。旃檀本是方圆千里闻名遐迩的少年英雄,又配以如此宝剑,英姿勃发、风临玉树,时人惊之为天人。
且说那两剑相交,发出激昂有力的铿锵之声,剑风所偏倚之处,连百十斤重的檀香木椅都被掀了个跟头。陆扬退了三步、旃檀退了两步,皆道:“好内劲!好剑法!”
陆扬自出道以来,从未遇见过如此敌手,心道:“旃檀兄剑法不错,内力更是深厚,完全不像是二十刚出头的少年人物能有的精熟内力,竟能同师娘的醇厚内劲相比拟。一味的守御难免落败,不如出其不意,攻他一攻!”便将青钢剑一抖,一招“虹贯白堤”,那剑便如银蛟一般直直取向旃檀紫宫一穴。旃檀赞道:“来得好!”把着剑左劈右削、右劈左斫,似是在演练一套繁复的剑法,陆扬细细一看,却又看不出路数来,避了锋芒,一招梅坞茶采,几点剑芒便如飞飒流星一般赶到。
旃檀笑道:“陆兄,看我这一招浪遏飞舟!”那玄剑便如壶口巨浪一般,滔天袭来。陆扬所使出的几点剑芒似是湮灭在了这汹涌的巨浪中去了。众人见陆扬形式处下风,皆为陆扬捏了把汗,朱晋廷在座上向陆银桂笑道:“不瞒师姐,这浪遏飞舟一招可是极其克制贵派梅坞茶采此类精妙剑法的,看似毫无章法,却又处处掣肘,陆扬贤侄此时境况不妙啊!”陆银桂淡淡道:“师兄莫要担心,江南多弄潮儿,且看我那徒弟如何去应对。”话音未落,陆扬却攻势愈发猛烈起来,剑尖各处点得极为精准,差了一丝一毫便全局皆乱。
杨金熠赞道:“陆贤侄打的可是一个气势啊!年轻人傲气,终是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,可不像我等上了岁数的人咯,总要细细打打算盘才能出手的。”
朱晋廷道:“瞎说!我俩算是不年轻咯,银桂师姐可还风华正茂呢!”二人哈哈一笑,陆银桂心里也觉得有趣,嘴上却只是轻轻哼了一声。
旃檀见陆扬一直出剑,自己虽然使那浪遏飞舟,总归较为保险,却怕陆扬剑招中的虚招奇诡,万一不留神,教他点了破绽,自己难免要落败的,便回转剑势,笑道:“陆兄,此一剑!”剑眉紧锁,星目流光,玄衣飘然,便挺剑直直刺了去。陆扬收了把式,笑道:“正合我意!”,吟道:“曲院风荷举,倩谁浣鲛纱!”一招“风荷举”,便也直取旃檀。
旃檀飞身前去,一招“大河之剑”,剑风飒飒、势如破竹;陆扬纵身跳来,一招“风荷举”,婉约优雅却又带着肃杀之意。缘那“大河之剑”乃是朱晋廷远涉西夏,于那黄河之源所悟得的无上剑招,后又经过朱旃檀于壶口临瀑观悟,加以改良,便成了壶口剑诀的一大杀招。大河之意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!二人兵刃相交,内力激荡,剑却没发出半丝声响来,想来双剑竟是被二人的内力所粘合住了!正因于此,二人的也动弹不得,只是全神贯注地维持着那僵局,谁都不敢进一步、退一步。
剑拔弩张之时,堂口却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孩儿声响来:“那么好看的比试,爹爹和朱叔叔就是偏心,总不让我看!”杨金熠一听这不怕天不怕地的清亮嗓子,鼠须也拈不住了,苦笑道:“小妮子,怎么跑这儿来了?女红做完没有?”缘是杨金熠的女儿杨舒窈,一个人呆在闺房中闲得无聊,几位侍女又不敢招惹那刁蛮大小姐,只让她一个人摔摔织物、划划琴儿罢了,窈儿见大堂中热闹,便使了轻身法子,腾挪到此处来了。窈儿一撇嘴,敷衍道:“做了,做了啦!”便看向陆扬与旃檀,笑道:“那书生同旃檀哥怎么像木头人一般一动不动的,真好玩!咦,那位公子我好像见过的……”
朱晋廷笑道:“小妮子又胡说八道!你深居闺阁,又怎会见着陆扬师侄?”
陆扬一听这嗓儿,便认出了来者,心中一惊,手也抖瑟了一下——晋廷师叔啊晋廷师叔,您口中那位“小妮子”,可不就是昨日里诓我饮酒的上官青云嘛!谁知她竟是杨家的千金!哪知陆扬二人正处于水火相济的要紧处,一丝一毫的分神,霎时便会扭转势均力敌的局势。而旃檀正全神贯注之时,以人入剑,以剑入势,一下收不住,大叫一声:“小心!”陆扬眼睁睁见旃檀玄剑刺来,形势紧迫,急要辗转,却又抽不出身来。婉儿也见势头不对,惊呼一声,便欲前去相助,陆银桂知就凭婉儿的修为,去也是帮倒忙的,拉住了婉儿,自己也欲起身解围。至此千钧一发之际,几粒算珠便如惊雀一般飞来,极为准确地将旃檀的来剑点住。缘是杨金熠见二人比斗内力,便如那二牛斗墙下一般,终有一人会“盛气不泄毕”的,便暗藏几粒算珠于袖内,见势头不对了,还能出手干预。
且说杨金熠使了一招“乱瀑飞珠”,将旃檀的玄剑给格挡开来了,旃檀用力不稳,往后直退了七八步方才站稳,忙道:“陆兄,小弟学艺不精,收不住力,适才冒犯了!”陆扬更是难堪,正想扭身躲避来着,力忽地消了,身子无处可借力,飞了出去,正好飞到杨舒窈的脚边。陆扬一见杨舒窈,也不起身,便单膝跪地,抱拳道:“前日里冒犯姑娘,多有得罪,可望姑娘海涵。”见窈儿今日里换上了女装,着了一身百褶如意月裙,修眉青黛,目流秋波,肤如凝荔,明媚鲜妍不可方物,心里道:“窈儿姑娘又有英气、又有灵气,真是好看,自然同婉儿是两种风流。”两位少年郎方才还在举剑相斗,此时却各自抱拳道着歉,众人皆是摸不着头脑来。
此时窈儿也认出面前俊朗的书生竟是昨日那位不端的“登徒子”,柳眉一蹙,正欲发作,杨金熠却道:“窈儿!还不把你陆扬师兄扶起来!”窈儿跺跺脚,气道:“爹,他……”却说不出话来。
陆扬自己站了起来,向旃檀道:“武力不及旃檀兄,心服口服!”朱晋廷叹道:“你二人本是功夫相差无几的,这一战,我等浸淫江湖数十年之人,看来也觉得精彩。可不知为何陆扬贤侄忽地乱了功法,不然谁胜谁负,仍未可知呢。可惜,可惜!”
杨金熠也可惜道:“可惜了我那两颗珠子,定是散成齑粉了!赔本买卖!”又捻了捻自己的鼠须儿。
婉儿却急忙跑来,扶着陆扬关切道:“没伤着吧?”话音未落,便意识到有那么多长辈看着呢,忙红着脸放开了手,只是道:“快坐下休息会儿。”陆扬笑道:“我又不是春风杨柳一般的人儿,不碍事。”随即从衣衫中掏出一只锦囊来,道:“上官……不,窈儿姑娘,你的精铁牡丹在这儿,物归原主了。”
窈儿一惊,看向旃檀,旃檀正抱着玄剑,笑吟吟地看着他们。窈儿脸红得像是能沁出血来一般,一把将锦囊抢了过来,狠狠白了陆扬一眼,便飞也似地跑走了。杨金熠摇头道:“小女向来不识礼数,让各位见笑了。”旃檀也走来,携着陆扬的手道:“好剑法!好侠客!今晚小弟做东,我二人好好喝一杯!”陆扬看向陆银桂,陆银桂面上似是有些冷,微微颔首,似是不置可否。陆扬笑道:“那就麻烦旃檀兄了。”见朱旃檀武功也高,人也谦卑,不禁对其生了些好感来。只是婉儿在旁边幽幽道:“你……怎么说来着?”
陆扬忽地想起自己的话来,顿时有些难堪,挠挠头道: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婉儿叹了口气,徐徐道:“别喝太多了。随你吧。”便移步回到了陆银桂身旁。
得了师娘首肯,又能同旃檀此般俊杰之士痛快饮酒,婉儿似乎也不生气了,连那精铁牡丹也物归原主,陆扬经历了如此恶战,浑身却暖洋洋的,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。堂内三位前辈似是要谈些什么事儿,陆扬也随旃檀进里屋论些江湖、漫谈剑之一道了。只是陆扬心里仍还存着些莫名的情愫,看见过路配剑丫鬟的身影,却总能想起那个毛手毛脚的女孩儿来。
虽过两日才是龙城义贾杨金熠的诞辰,整个朱府却早已张灯结彩、金碧辉煌,缘那朱杨两家平日里相交甚密,不分彼此;朱晋廷更将壶口剑派的总坛安置在了自己府中,是故杨金熠虽时常做些典当生意,富可敌国,人脉也广通八方,却依旧落户于朱府,也算任个幕僚、传功掌门之类的职务。因此,窈儿同旃檀算是从小便搁一处长大的玩伴,待长得更大一些了,旃檀便拜杨金熠为师,学那壶口剑派乃至天下各处的玄妙武功,也抽不出身来再同窈儿如孩提时那般玩闹,二人看似渐渐疏远了起来。然而在闲暇时候,旃檀也曾悄悄教过窈儿几式粗浅的功夫与一套名为“镂月裁云”的轻身法子。在窈儿眼中,旃檀似乎总有永远忙不过来的各类事务,却终归是个懂得疼自己的大哥哥。
杨金熠守旧,自己虽然武艺高强,却从不准窈儿学上半点武功。在他眼中,女孩儿大可不必牵扯到武林纷争中去,在闺房中抚抚琴、做做女红调养心性即可。谁知窈儿向来是个难伺候的主儿,女红做得乱七八糟;琴搁着搁着,也成了块烂木头,自己却对外面的江湖极其向往。旃檀拗不过小妹的胡搅蛮缠,便时常说些江湖趣闻博之一乐,窈儿心中更是如小猫挠了一般痒痒,总想出门看看。谁知这第一次溜出门去,倒撞上了陆扬,倒也令人啼笑皆非了。
且说旃檀引陆扬到别院,二人对坐下来,又说了些江湖见闻。时辰已经不早了,早有小厮把酒菜安排上了,旃檀便亲自提了酒壶,斟了杯酒送给陆扬,自己也举杯道:“陆兄,来,好汾酒!小弟早有听闻过的,南屏诗酒剑,好诗好酒好剑,乃是书生般儒雅潇洒的剑客。小弟平日里不好饮酒,今日就破例同陆兄喝上两杯!”
“承蒙旃檀兄厚爱,无以为报,饮酒便是!”陆扬哈哈笑道,自己先饮了一杯下去,只觉喉头似是被晶莹温润的美玉抚过了一般,一咂嘴,满口都是谷物的余香,不禁赞道:“这汾酒又是一番滋味出来了。想来定与市上所鬻成品不同。”
旃檀笑道:“陆兄果是好眼力!这汾酒乃是我家窖藏百余年,同我辈先祖自那洛阳一同颠沛流离而来的。咦,陆兄乃是江南人氏,又如何饮过汾酒?”
陆扬哈哈笑道:“可是托了令妹的福啊。”便将昨日天香楼头之事同旃檀细细说了。旃檀抚掌笑道:“妙极!妙极!万事皆讲究个缘法,看来我二人奇缘不浅呐!来!”
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。春山月明,花影阑珊,二人推杯换盏,渐渐也饮了有半个时辰。陆扬倒还轻松,但觉酒力下沉气海丹田,同那南屏山意一经混淆,阳归阳,阴归阴,但觉浑身暖流涌动,寒气具散;连带口舌生津,灵台清明。旃檀平日里不大饮酒,只是饮了几杯,脸上也渐渐沁出红晕来,带了几分狂意,将如瀑般的墨发倾洒而下,清夜星月一般闪耀的眸子中也似是曜着亮色,举酒道:“痛快!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!”
陆扬也接口道: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也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但愿诗酒趁年华,不负平生意!”不顾平日里儒雅样子,敞开衣襟口子来,笑道:“以往总是囿于南屏这小小一处,如那笼中鸟儿,不得自在。今日里能结识旃檀兄如此俊杰,把酒言欢,吟赏花月,真真是人生一大乐事!”
旃檀将酒樽杵在石桌上,沉默半晌,醉醉道:“陆兄又岂是笼中燕雀、池中凡鳞?当有一日乘雷化龙!旃檀自念平生所见的剑道天才屈指则能数之,末学恐难忝名其列,假以时日,陆兄定能以手中这把青钢剑,以精巧绮错的南屏剑法登上武林的顶峰!”
陆扬羞赧道:“旃檀兄此言过矣。武修恒无止境,剑道袤似沧海,就算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侠客,又有谁能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已到了武林的顶点呢?久闻少林枯木大师以少林七十二绝艺同那劲力雄浑的‘枯木意’成就天下第一宗门,龙虎山希声道长阴阳要妙三十剑变化莫测、难以捉摸;南屏剑重拆招卸招,大河剑依仗大河剑意纵横捭阖、无往不利。鄱阳五派四海剑阵密不容针,打蛇帮醉踏云霄妙至毫颠,三招苍云蛇拐精奥难言;更有那弹铗剑歌白忘川,虽已退隐江湖多年,一手弹铗剑歌依旧名烁江湖……且不说这些前辈高手,旃檀兄名曰壶口剑侠,适才领教了一下名誉天下的大河之剑,方觉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!旃檀兄这般俊杰面前,小弟安敢班门弄斧、自夸武林顶峰云云?”
是哇,天下英雄何其多尔,武道追寻永无止境,陆兄大可不必过谦了。可我这晋北大河剑……又怎堪陆兄所云这般的光鲜?呵!”旃檀借着酒意苦笑道,“众人皆道我朱旃檀壶口剑侠、壶口剑侠的,谁知道我又侠在了哪儿?我要这玄剑,又有何用?”
陆扬轻抚着旃檀的背脊,柔声道:“旃檀兄慢慢说。今日你我二人一见如故,又承蒙厚爱,请教了旃檀兄的壶口一剑,还饮了如此好酒,叙话也好,交游也罢,往来几十年亦能期许。我二人本是世交,小弟更愿以棠棣之谊待君。且说无妨。”
旃檀又饮了口酒,摇头道:“诗酒趁年华,谁又不愿如此呢?要能携三五伴侣,江湖游荡,快意平生,谁又不想呢?只是小弟生于此间,便注定要承那家国大事的!陆兄你可知,十年前,那赵匡胤将我朱唐一脉赶离太原,赵匡义又一把火将我晋阳龙脉烧得满目疮痍,圣寿、龙泉,金胜、西山,一处也不留啊!得亏父亲携大小家眷钻了城门狗洞,仓皇而逃,我朱唐一脉香火才得以苟全。此间本是我朱唐家的不传之秘,于陆兄而言,说了倒也无妨。小弟姓名朱旃檀,旃檀旃檀,便是那展唐的意思!”
陆扬听得此语,攥了旃檀的手,动情道:“是了!不瞒旃檀兄,小弟早失牯恃,好赖师父师娘养大,不然早已冻死南屏山下也。师父云游未归,师娘常恨赵姓之人,每有弟子入门,是必吐口唾沫到那赵匡胤画像上!我二人说来,也算是同仇敌忾了!”
旃檀叹道:“如此甚好!可是……我又何尝要去当那帝王!”
陆扬讶异道:“旃檀兄所烦恼之事,便是如此?”
旃檀道:“不瞒陆兄,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,皆是不得已之事。”
陆扬摇头道:“此言谬矣。贞观年间,有慧能大师作偈语云:‘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’应无所住,而生其心,既然万物万事皆非永恒,又何必执着于什么不得已之事呢。”
旃檀苦笑道:“陆兄说得可轻巧。天降大任,列祖庇荫,此缘至深,又何以断之?”
陆扬道:“只愿不勉强,任由心走,便是了。”
旃檀忽地将酒杯一顿,沉声道:“我……偏要勉强!所以我也艳羡陆兄啊……一身青白,一壶潇洒,一剑自在,一生不羁!无案牍之累,无夙愿之烦;无劳形之事,无逐利之心。想来就来,想去便去,又管那些劳什子作甚!而我,我朱旃檀,注定是要承列祖遗志,配那玄剑也是,冥冥之中,就为了云起龙骧,成就一番无上的伟业!”
陆扬道:“旃檀兄别想那么多,且饮酒便是。”
旃檀笑道:“小弟酒力已经不胜,平日里饮酒最多不过三杯。这酒啊,一日里只可饮三杯,饮多了,一时的潇洒,一不留神,怕会断了祖宗的基业!”
陆扬心道:“旃檀兄隐情匿性,明明是愿意浪荡江湖的好侠客,却因先天缘法而心生执念,就这样受困囹圄,实实大不易。”
旃檀站起身来,抱拳道:“今日里把盏寻欢、促膝长谈,甚为快意,小弟实在高兴。不瞒陆兄,往日旃檀所结交之辈,虽有一二得趣者,大多却只是一派披着侠客外皮的土龙沐猴罢了。今日一交陆兄这般有功夫、有风范的侠客,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也。正因如此,才将此般秘辛告诉了陆兄。只是小弟——”顿了顿,却郁郁叹了口气出来。
陆扬见旃檀犹疑了一下,却道:“旃檀兄但说无妨。”
旃檀那具着黑曜石般光泽的眼眸直盯着陆扬,手指颇有节奏地敲着手边的玄剑,微微侧了侧头,黑曜石般闪烁的眼眸中似是倒映着满天星河的光芒。半晌,旃檀回过了神来,抚了抚腰间的神兵玄剑,向他笑道:“思来想去,还是到时候再同陆兄说起此事罢。夜迟了,小弟暂先就寝去,告辞!”复又仰天长啸道:“弓背霞明剑照霜,秋风走马出晋阳。未收天下河湟地……不拟回头望故乡!”哈哈笑着,便一个纵身,飞回了屋内。
陆扬又呆坐了一阵,心中不住想着:“旃檀兄何必此般踌躇?我二人虽彼此意气相投,说来也只是结识了一朝一夕,他又奈何将自己胸中的复国大计向我全盘托出?想他虽口中说不大出,最后那四句诗却……唉,旃檀兄啊旃檀兄,我又何尝不知道你想说些什么呢。可是——若不帮你呢,一位大好的潇洒侠客被此般心魔所困,我心中也有怜悯;更不说旃檀兄如此嘉友,将此般隐秘之事与我说了,不去两肋插刀,道义上也说不过去。可若要帮旃檀兄,不怕自己卷入那纷繁错杂的派系之争去,却只怕不能再快意饮酒、笑傲江湖了。”
陆扬沉沉叹道:“朱旃檀哇朱旃檀,不知该说你是太聪明了,还是太赤诚了呢!”站起身来慢慢踱着,一时也拿不定主意。不知不觉,竟走到别的一处院落中去了。那院落四围灯火皆是熄了,左厢房却幽幽地亮着一团烛火,屋内似是有二人正在对酌,低声叙着些话儿。搁平日里,如此瓜田李下之景,陆扬定会远远躲开了,以免滋生事端。可独独今日,心里想着事儿,饮酒后也不知轻重,陆扬自顾自走着,却不知不觉走到了那厢房墙下。
“……怎样,明日里天下武道大会,安排的还妥当吧?此番绝不可出岔子!”陆扬隐隐听这声响,似是那壶口掌门朱晋廷所说的。
“你何时见我失过手?”陆扬透过窗帷看去,似是杨金熠在说话。
“也是,也是。交给你龙城义贾来做,心里当然是一百个称心如意的。明日里再看看各派有多少青年才俊,能为我所用的,便想尽一切办法招揽来!”朱晋廷笑道,随即沉吟片刻,一字一顿地念道:“数年徒守困,空对旧山川。龙岂池中物?乘雷欲上天!”
“数年徒守困,空对旧山川。龙岂池中物?乘雷欲上天!”杨金熠捻了捻自己的鼠须,似是品味出了些什么一般,也跟朱晋廷念了一遍。
“百年啊,百年!我大唐定能重振雄风!”
“百年!”杨金熠也道,声音有些颤抖,“难以想象的隐忍与付出!赔本赚吆喝,花了多少银子,招徕了多少势力,终是打通了如此人脉,大义不举,枉对列祖列宗!”
“我朱晋廷取了此名,便是定要在晋北龙城建立起属于自己自己的朝廷的!”朱晋廷斩钉截铁道,“绝不枉列祖列宗百年的流离颠沛!”
“明日做寿,成败在此一举了。各处关节皆已打通。秦晋一带的江湖已被旃檀平了,当年你远赴川贵,也将那千里一毒的噬毒门收了下来,只余下齐鲁、皖赣两处的人马了。陆银桂油盐不进,吴越一带只能从陆扬这儿下手了。旃檀懂事,你看,今日里不打不相识的,现在还在后院饮酒叙话儿呢。窈儿看起来同陆扬也认识,我看不如……”杨金熠揣度道。
“老杨,莫要再说!我见窈儿这孩子似是对旃檀有些意思。你的女儿,还是莫要掺和进去较好,或许吴越一带有另的法子呢。不必让窈儿如此……。”
“欸,江湖一事,又何必牵扯到什么儿女情长。”杨金熠似是极为怅惘,叹道。
“杨兄,你对我朱唐兴国之事,可是太过上心了。我朱唐事成之时,便是你杨金熠拜相之日!”朱晋廷似是有些感激,颤声道。
“无妨,无妨。”杨金熠淡淡道。“还是称帝重要些,这女儿在我眼里,强似一枚棋子罢了。我等几十年的大好年华啊,总不能熬到空处去了!”
陆扬有些呆住了,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,绝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父亲。
“今日终是见了陆扬,怎么样,可有打算?”朱晋廷顿了顿,忽道。
陆扬一听谈到自己,忙凝起神来,细细听着。
“坏买卖!那陆金戈欠了陆扬多少银钱,自己逃了如山债务,跑去荒山野岭里躲起来了,却让陆银桂来还呐。”杨金熠笑嘻嘻道。
“江湖,唉,江湖!”朱晋廷叹道,“我们可算了十几年的账了。也不知那陆金戈是死是活,是否又在算计我呢。我看呐,他是不知道躲到哪儿了,好研究那本……哈哈,此人机心缜密,可是工于心计得很呐,你可知他连亲兄弟陆不器都要算计,还忽悠了自己的可怜虫侄儿十几年的时间呢!”
陆扬头上似是被熟铜宣花锤子狠狠砸了一下,似乎能隐约听出些门道来,双手微微有些颤抖,趴在窗沿上,想听,却又不敢再听下去了。
“陆银桂倒是心善,将陆扬视为己出的。”
“我看是有愧于陆扬吧!自己丈夫心狠手辣,将兄弟一家给净屠了,留着陆扬当火种儿,还搭上自己闺女陆婉儿,就只为那无上法门、那吴越王位?陆金戈可不姓陆,陆扬也不姓陆,他们姓钱!是那吴越国王钱镠之后!”
陆扬似是受了五雷轰顶,想起陆银桂时常说的“不谈钱姓人”,脑中更是有些混沌了。自己又饮了酒,在门外久了,风也受了不少,一个踉跄,便造出些声响来。屋内二人齐声道:“谁?”便飞身推门出来。陆扬早知不妙,一步“云间飞雀”,飞上屋檐。即使陆扬将脚步压得很低了,朱晋廷二人听声辨位,却也纷纷飞了上来。陆扬知道自己论轻身法子定是比不过那二位武林前辈的,情急之下,见脚下门屋半掩,也不知青红皂白,硬生生就挤了进门内。
陆扬一进那屋内,便闻到一股子浓郁的牡丹香味,仔细一看,南边墙上挂着几把形象各异的宝剑,明晃晃地亮着青光。夜已深了,东风骀荡,却依旧拨过未关严实的雕花木窗,拂弄着台上斜摆着的一把焦尾琴,焦尾琴上还覆着一片粗糙的、仍未完成的女红,陆扬定睛一瞧,姹紫嫣红一团团乱糟糟的,还没有婉儿做的一半好看。边上鼎炉里升起了袅袅的香烟,卷裹着西面的红纱帐,就连纱幔中侧身卧着的袅娜身形,也被氤氲的香雾渲染得模糊起来。
陆扬见得此情此景,酒也被吓得醒了一大半:这十有八九就是一位女子的香闺啊!凭朱晋廷与杨金熠的本事,要找到他简直易如反掌,只怕自己到时有百十张嘴,也分辨不清楚了!
就在这时,门口飘来一道人影,杨金熠似是已经赶到,立在门口,迟疑了片刻,却不推门进来。陆扬见四处无可藏匿,形势所迫,乘着酒劲,撩开红纱帐,一招“鱼跃龙门”,便如鲤鱼一般滑进床纱中去了。那门口人影顿了一顿,举手敲了敲门,陆扬怕床上女子惊醒了,暗道一声得罪,忙使巧劲,盲点了她四处穴道,叫她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门口那人又立了半晌,陆扬如一只惊弓之鸟,只觉胸口似小鹿乱撞,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,忙提起气来,屏息凝神,以不变应万变。那人似是轻笑了一声,随即抖落了什么东西,像是算盘轻摇的声响,便慢步踱远去了。陆扬听那渐行渐远的脚步声,如历仙纶梵音,渐渐也松了口气下来,只觉得背上湿湿的。陆扬奇怪,转身一看,一个女孩儿瑟缩在被中,也不得动弹,修眉紧蹙,一双明晃晃的眸子正泫泫然氤氲着些水雾,恨恨地盯着他。陆扬此时酒倒是醒得十有八九了,也认出来身旁女子的模样来了,不禁惊得轻呼出声:“窈儿姑娘?!”
未完继续……
前情提要:
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三等奖:诗酒趁年华①
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三等奖:诗酒趁年华②
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三等奖:诗酒趁年华③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| |